2025 HCIC采访间|马量教授对话姜胜利、吴连拼教授:瞄定瓣膜病治疗的抉择热点,开启内外科前沿碰撞
2025-08-22 19: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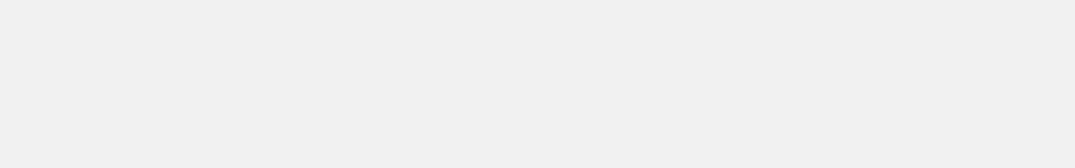
心脏瓣膜病治疗已形成外科手术与经导管介入并重格局。随着介入技术成熟,其适应证正快速向传统外科治疗的低中危患者扩展,由此引发优选策略的核心争议。这一临床抉择困境亟需个体化评估与多学科协作破解。
本次大会精心打造的采访间突破会场物理边界,成为沉浸式学术互动的典范。受邀专家在此实时分享学科融合的独到见解,将前沿思考与人文情怀传播向更广阔领域。
本次采访间荣幸邀请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马量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姜胜利教授和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吴连拼教授,聚焦外科手术与TEER技术在低中危患者中的抉择困境以及年轻主动脉瓣狭窄患者的术式选择等热点问题展开深度对话。


扫码进入微官网
查看完整采访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