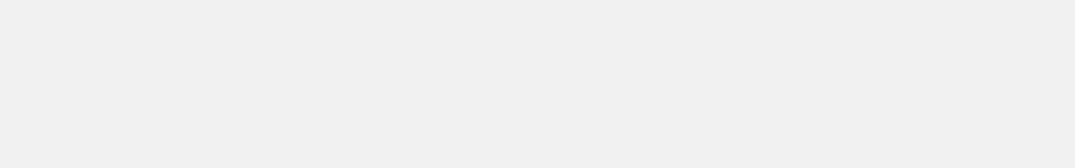
围产期心肌病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疾病,发病率为每3000至15000例活产中1例,主要发生在妊娠最后一个月或产后5个月内。已确定的危险因素包括黑人种族、多胎妊娠、产妇年龄>30岁、双胎妊娠以及高血压、子痫前期和子痫病史。预后取决于左心室收缩功能在初始发作后数月内的恢复情况。死亡率非常高,可达50%,心脏移植仍是最后的治疗选择。围产期心肌病的特点是左心室扩张伴整体心室功能障碍和射血分数(EF)显著降低,导致急性心力衰竭的典型临床表现。对于临床医生而言,区分围产期原因(如子痫前期、妊娠期高血压或围产期心肌病)和其他导致心脏衰竭或肺水肿原因(如应激性心肌病、既存心脏疾病包括二尖瓣狭窄、羊水栓塞或肺栓塞,甚至嗜铬细胞瘤)可能具有挑战性。近日,《BMJ Case Rep》报道了一例极为罕见的围产期嗜铬细胞瘤和席汉综合征同时发生的重症病例。

产后嗜铬细胞瘤危象伴心源性休克及席汉综合征
Postpartum pheochromocytoma crisis associated with cardiogenic shock and Sheehan’s syndrome
当两种罕见病在围产期相遇
妊娠期嗜铬细胞瘤比围产期心肌病更为罕见,估计发病率为每15000至54000例妊娠中1例。然而,若未诊断或未治疗,产妇和胎儿的并发症发生率很高,母婴死亡率可达40%-50%。
这种内分泌肿瘤伴有多种症状,包括高血压、头痛、心悸、多汗、肌肉震颤、呕吐、惊恐发作、血管舒缩障碍和视力模糊。据报道,高血压是妊娠期嗜铬细胞瘤最常见的临床表现(88%);然而,三分之一的受影响女性在产前已有高血压危象。
另一种罕见的产后疾病是席汉综合征,表现为因分娩或分娩后缺血或出血导致的垂体坏死所致的垂体功能减退。该病于1937年由Harold L Sheehan首次描述,由于症状非特异性,如嗜睡、闭经或泌乳问题,通常多年未能得到诊断。每个垂体轴都可能受到影响,但最常见的是泌乳激素和生长激素缺乏,后者可能是由于生长激素细胞位于外周,最易受缺血性坏死影响。
垂体功能减退通常不可逆,某些垂体功能可能在妊娠后数年恶化。治疗通常采用受影响的垂体轴的激素替代。
据我们所知,这两种罕见内分泌疾病——嗜铬细胞瘤和席汉综合征同时发生的情况,此前从未报道过。
病例报告
危机的开端:被误读的“惊恐发作”
一名30多岁的孕妇在妊娠41周时入住奥地利一家医院,并顺利足月分娩第二胎。除反复惊恐发作和心悸约4年外,其既往病史正常。
分娩后6小时,患者出现恶心、心动过速和呼吸急促,外周血氧饱和度下降(85%),需要吸氧。随后,患者被转入当地重症监护室(ICU)。CT未发现肺栓塞迹象,但显示严重肺淤血和右上腹部9×9.5厘米的分隔囊性肿块,被解读为出血性肾囊肿。
尽管进行了利尿治疗和无创通气支持,在接下来的数小时内患者的呼吸状况恶化,不得不进行气管插管。插管后不久,患者出现心源性休克,需进行机械心肺复苏(CPR)。恢复自主循环后,床边超声心动图显示左心室功能严重受损,计算得出的示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低于20%。基于这些结果和临床表现,怀疑为围产期心肌病,患者的循环由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ECMO)支持(插管部位:右股静脉+右锁骨下动脉,ECMO支持流量3.5 L/min;转速3000 rpm;吸入氧浓度60%;气体流量2 L/min)。
关键转折:从“肾囊肿”到嗜铬细胞瘤的证据追踪
由于心脏功能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未改善,我院被紧急邀请进行高优先级的心脏移植。为评估神经功能,患者停用镇静和机械通气,拔管后没有显示神经功能缺损迹象。因此,患者被转至我院心胸血管外科ICU进行心脏移植评估。入院时,患者完全依赖ECMO支持,但意识清醒且自主呼吸。超声心动图显示左心室整体运动减弱至无运动,左心室功能严重受损,但右心室功能、瓣膜正常,心包积液1厘米。NT-proBNP显著升高至1852.6 pmol/L(0-14.7 pmol/L)。
鉴于需要评估Takotsubo心肌病或其他未知潜在可逆性急性心肌病的鉴别诊断,患者未被立即列入心脏移植名单。最初,患者出现反复血流动力学波动,伴有高血压和严重低血压发作,需分别间歇给予血管扩张剂和血管升压药。然而,入院后几天,超声心动图检查显示左心室功能持续改善,从而允许逐步停用体外循环支持。尽管如此,为排除主动脉损伤,进行了CT检查。CT扫描未发现主动脉夹层,但显示右肾区域有一个9×9.5×10.5厘米的大型低密度囊性肿块,此前在外院CT扫描中怀疑为出血性肾囊肿。
CT还显示右肺上叶肺动脉栓塞和双侧髂静脉大血栓,很可能是由于ECMO插管处的血栓所致。患者无肺栓塞典型症状,但随后接受了抗凝治疗。
由于右上腹报告有肿块,患者有惊恐发作和心悸病史,且近期发生血流动力学波动事件,遂进行了内分泌检查,发现血浆甲氧基肾上腺素(MN)和甲氧基去甲肾上腺素(NMN)水平显著升高,高度怀疑嗜铬细胞瘤(见表1)。
表1. 产后及肾上腺切除术后实验室检查结果。

为确认这一诊断,进行了MRI和F-DOPA PET/CT检查,显示右侧肾上腺区9×9.5×10厘米囊性出血性病变,F-DOPA摄取明显,符合右侧肾上腺嗜铬细胞瘤(见图1)。

图1. MRI(a)和F-DOPA PET/CT(b)均显示右上腹部囊性肿块。PET扫描中F-DOPA摄取阳性(b)证实了出血性嗜铬细胞瘤的怀疑。
隐匿的双重打击:席汉综合征的逆向诊断
此外,患者出现低钠血症(127 mmol/L,136-145 mmol/L),血清促甲状腺激素正常低值,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和游离甲状腺素(fT4)降低,提示中枢性甲状腺功能减退,可能伴有肾上腺功能不全(见表1)。因此,分析了垂体激素,发现垂体前叶功能完全丧失,伴促甲状腺、促肾上腺皮质、促性腺和生长激素缺乏,但无尿崩症(见表1)。因此,除嗜铬细胞瘤外,患者还表现为产后垂体功能减退,提示席汉综合征。垂体MRI显示前垂体叶的大部分坏死,符合垂体梗死和席汉综合征表现(见图2)。未发现垂体内出血的信号变化。开始氢化可的松(20 mg)和左旋甲状腺素(50 µg)替代治疗后,血清钠、fT3和fT4水平迅速恢复正常(见表1)。

图2. 垂体MRI矢状位(a)和冠状位(b)T1加权像增强后显示垂体前叶中央无增强(箭头),呈边缘增强,符合垂体坏死表现。
血流动力学状况保持稳定,心输出量完全恢复正常后,患者转至普通病房。由于近期肺栓塞需抗凝治疗,嗜铬细胞瘤手术不得不推迟。因此,患者开始服用最高耐受剂量的α受体阻滞剂(多沙唑嗪),并出院。3个月后,通过开腹手术完整切除嗜铬细胞瘤。组织学检查显示右侧肾上腺出血坏死性嗜铬细胞瘤,分化程度低,转移可能性大。
鉴别诊断
嗜铬细胞瘤诱发的心力衰竭与其他形式急性心力衰竭(如围产期心肌病)的鉴别诊断可能构成临床难题,因为症状和超声心动图特征可能非常相似。然而,反复出现高血压发作和心律失常病史,尤其是在妊娠前,可能提示嗜铬细胞瘤而非围产期心肌病。另一种可能的区分方法是症状初始发作时间。尽管嗜铬细胞瘤相关急性症状在妊娠后期更常见,但也可能在妊娠早期出现。相比之下,围产期心肌病是在妊娠最后一个月至产后5个月内发生急性心力衰竭。
结局与随访
患者已在内分泌门诊随访4年。她健康状况良好,已重返工作岗位。遗传性嗜铬细胞瘤基因检测,包括SDHB、SDHC、SDHD和RET基因,以及全外显子测序,结果均为阴性。术后血浆和尿液中MN和NMN浓度保持正常。F-DOPA PET/CT扫描每年进行一次(根据患者强烈意愿),未发现残留或复发嗜铬细胞瘤。两次随访垂体MRI(最近一次在初次诊断后3.5年)显示空泡蝶鞍,残留垂体极小,垂体柄位于蝶鞍内保持完整。
患者仍在接受氢化可的松、左旋甲状腺素和性激素替代治疗。然而,左旋甲状腺素剂量已减至25 µg,提示中枢性甲状腺功能减退已部分恢复(见表1)。随访现每年进行一次。
讨论
妊娠期或围产期嗜铬细胞瘤危象是极为罕见但危及生命的并发症,目前尚无临床指南指导此类危急情况的处理。产后嗜铬细胞瘤的诊断使母婴不良结局风险最高。因此,妊娠合并嗜铬细胞瘤的妇女在分娩时最为脆弱,因为胎动、子宫收缩和分娩可引起儿茶酚胺释放,导致心血管急症。儿茶酚胺激增和高血压发作还可能破坏胎盘循环,导致胎儿缺氧甚至流产。
总体而言,嗜铬细胞瘤的诊断常因该病罕见及临床表现非特异性而延迟。尤其在妊娠期间,高血压作为嗜铬细胞瘤的主要症状之一,可能被误诊为妊娠期高血压。然而,对于妊娠早期出现高血压危象或新诊断高血压的妇女,应考虑嗜铬细胞瘤的可能性。本例患者中,妊娠前后出现的高血压发作被归因于惊恐发作,而惊恐发作也可能是嗜铬细胞瘤的症状。即使在妊娠期间可能无法进行全面的继发性高血压诊断检查(辐射暴露原因),但激素分析是可行的,若怀疑嗜铬细胞瘤,应进行检查。
嗜铬细胞瘤手术时机的争议与共识
此外,建议对有嗜铬细胞瘤或副神经节瘤遗传倾向或家族史的妇女在妊娠前进行筛查。若妊娠期间诊断出嗜铬细胞瘤,建议进行药物治疗以避免高血压危象。α-肾上腺素能受体阻滞剂是治疗首选。可考虑在妊娠中期进行手术。然而,一项近期回顾性研究显示,手术并未改善母婴结局,需谨慎解读,因该研究存在回顾性设计、报告数据缺失、潜在选择和信息偏倚,以及部分中心非系统性入组等问题。该研究纳入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期间产科诊疗和嗜铬细胞瘤认识均取得显著进展。总体而言,该研究报告的母婴不良结局发生率明显低于以往报告,这进一步限制了关于产前手术与非手术治疗潜在风险的结论。
儿茶酚胺风暴的心肌毒性效应
嗜铬细胞瘤危象最危险的并发症之一是急性心力衰竭,如本病例所示。尽管确切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但有人假设儿茶酚胺水平升高或其氧化产物导致肌膜通透性增加,进而引起细胞内钙离子内流增强和心肌细胞坏死。
另一种假设机制认为,过度的肾上腺能刺激引起血管收缩和冠状动脉灌注减少,导致“缺血性心肌炎”。
ECMO是急性血流动力学衰竭的有效挽救疗法,但与高出血、血栓栓塞和神经功能损伤风险相关。本病例中,ECMO对患者有利结局至关重要,因为它避免了不必要的高优先级心脏移植,并允许进行全面的内分泌和影像学检查。
席汉综合征的非典型诱因:血流动力学波动主导的垂体缺血
在检查过程中,除嗜铬细胞瘤外,还发现患者存在席汉综合征伴垂体前叶功能不足。席汉综合征的垂体功能减退是由于分娩期间垂体坏死所致,最常见原因是分娩时大量子宫出血引起的出血性休克。本例患者阴道分娩顺利,无严重出血,因此子宫出血不太可能是席汉综合征的原因。然而,患者出现了心源性休克,需进行心肺复苏,很可能是围产期嗜铬细胞瘤危象导致的垂体灌注不良。此外,患者在ICU期间出现多次高血压和低血压发作,需间歇给予血管扩张剂和血管升压药,这可能进一步损害了产后脆弱的垂体灌注。妊娠期间垂体体积增大和鞍内压变化使组织特别容易发生缺血。因此,所有事实均指向嗜铬细胞瘤危象的血流动力学后果,是本例患者分娩后最脆弱阶段席汉综合征发展的关键。
诊疗挑战:从鉴别诊断到多模态治疗的精准抉择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罕见内分泌并发症,几乎使这位年轻女性和她的未出生孩子丧命。本病例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也凸显了由重症医学、罕见内分泌疾病诊断和此类罕见肿瘤外科治疗方面具有经验的多学科团队管理此类病例的重要性。例如,席汉综合征的体征在ICU患者中很容易被忽视,因为低钠血症和甲状腺激素水平异常在ICU患者中很常见。在未进行围手术期氢化可的松替代的情况下,对患者进行嗜铬细胞瘤切除手术,甚至紧急心脏移植,可能导致致命结局。
学习要点:构建罕见病诊疗的“三维思维”
嗜铬细胞瘤危象是妊娠期间罕见但危及生命的并发症。
妊娠期间出现高血压危象或新诊断高血压的妇女,尤其是妊娠早期,应考虑进行嗜铬细胞瘤筛查。
嗜铬细胞瘤患者应由经验丰富的多学科团队管理。
席汉综合征的体征容易被忽视,尤其是仅存在部分垂体功能减退时。
严道心得:把“罕见”变成“警示”
本例的特殊性不仅在于两种罕见病的叠加,更在于其揭示了围产期危象的“非典型路径”——无产后大出血的席汉综合征、以囊性出血为表现的嗜铬细胞瘤、可逆性心源性休克。这提示临床医生:在围产期这个“病理放大镜”下,任何不典型的血流动力学波动、难以解释的内分泌紊乱,都应启动“罕见病排查算法”。从最初的“围产期心肌病”误诊到最终的双重罕见病确诊,这一过程彰显了医学探索的本质——在标准诊疗路径之外,永远为“例外”保留思考空间。当多学科团队以机制为锚、以证据为帆,即使最复杂的病例也能驶向精准诊疗的港湾。